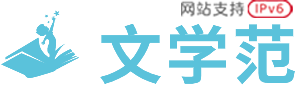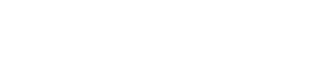和平已死?或和平已死。作为一种关系的理想化,和平,人类永恒的力求。先人借它构造了历史,在与“战争”共同充盈的史册里,它总是那么圣洁,完美,众望所归,以至于“战争”被映射的总是罪恶,肮脏荼毒生灵。事实又的确如此,人类对“和平”的热衷一向几乎“溺爱”,尽管“战争”时刻出现,但它的出现根基于人的被迫。发动战争者,不是为维护国家永恒不衰,就是满足人民之所欲,或是自身过激的“民族自强感”。谁与身好斗?“人之初,性本善”。人类潜意识下还是时刻憧憬和平的善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为“善之善者”,这种“和平速胜论”历来成为古代兵家的宗旨:诸葛亮北伐不间,“好战”源于白帝城托孤的“枷锁”,降敌作为首选,一直取代“下城”。多少场和平谈判,胜者以“威震四海”自诩,败者以“黎民百姓“自安”。一纸降书,避免了国家的灭亡,各处会谈湮没了战争的萌生。和平已死?然而,和平,是否又有它独有的本质?作为人类*后的精神寄托,作为姑且对现实世界的聊以自慰,战争后的调停者,往往载道的是,为战争圆场,为战争作嫁,亦或是孕育战争:一战后,列强拟定的和平体系,却换来了二十年后更残酷的二战;二战后,苏美规划的和平蓝图,掩盖了冷战的冰尖?迎来了各个区域的混战!和平,失其本质,有与无,便没了界限,畅和平者,懂和平乎?和平已死。
和平应死?或和平应死。竞争与和平,两种高尚的合作理念,人类不加以区分的同时,还乐观地自满融合。什么“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和平竞争”。不知道他们寻求什么,也许,在他们眼里,竞争者,可恶。更不明白,竞争和战争,又有何本质区别?对和平向往,畏惧如此程度,以至于,想方设法掩盖“战争”所表现的“残忍”,转型为“竞争”的“激烈”。并且,还套上“和平”的框架。的确,如此之后,人类在善化了的“竞争”中表现出的手段,也相继变为“实力、顽强”等等。心随即可安,已安之心必会放手一搏,且不说激励心志,和平使战争、竞争中的胜者,戴上成功的冠冕,站在历史浪头,响应先人,启发后人,谓之曰“治世英雄,乱世枭雄”。和平应死?既然竞争已是善化了的战争,二者强调的是“弱肉强食”、“唯己至上”。无论民族、团体、个人竞争,施展自己,置对方于必败之地,才是取胜之道,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然而,“和平”理论再将竞争善化,使竞争者涂上友谊的妆,压制自身争强的一面,近于“坐视垂成”,即消极竞争,如此和平,历史浪头一定会于空中泻下,未来全然不会有未来。和平应死。
死者比生者更受尊敬。人类对逝去的,更会同情、相信、怀恋。与此同时,对逝去的追念,总是那么绵长,明知道“一去不复”。和平时代的人不考虑下一场战争是否或何时到来,总是回首上一场战争与和平的轮回,企图从中获取些许警示,更妄想这和平的形式,可安己心。然而,空留和平的形式于世,其本质却死的彻底――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说是要爆发饿伊朗战争,那些发动战争者,打着“消灭恐怖主义,塑造无核世界,维护和平”的大旗,不知廉耻地将自己装点为正义的使者,与此同时,一些旁观者尽管嘴上发发牢骚,然而,行动上的麻痹,纵容这“和平”上演。战争的确单纯,无论何时,也不会失去自身的本质。相反,和平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本质已丧失殆尽。
用死者掩饰“罪行”,其罪更罪。
人类善化了“和平”,却又罪恶了“和平”。作为“悲剧”,和平,承受了太多。本质已亡,人类却不以为“和平”已死,形式的沉重,令其怎能荣耀,怎能延续?
血祭的祷告,刻在碑上,祭奠这人类的宠儿――和平。我愿和平真死,我愿和平的死,换来本质透彻的“原生态战争模式”。我愿和平死的安息。
我愿。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