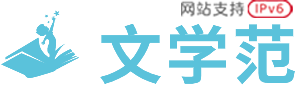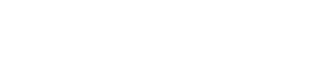小公园的围栏像是相约着逃离了这里,它们的同时消失并不会让人想到偷窃,倒像是一开始就不存在那些丑陋的低矮的围栏一样。年轻的疯子嚼着刚趴在地上啃食的枯黄的草叶,鼻子上残留的泥土在月光下闪着动人的光彩,它们和着他脸上棕红色的雀斑起舞,被乱蓬蓬的头发深深的盖住,这便在无意中加深了他在公园里的醒目。年轻的疯子很愉快,是的,他刚刚从愚人塔逃脱就像这公园里曾有的该死的围栏一样逃脱,他为此感觉整颗心都在强烈震动,直到现在也未缓过神来。
他欢快的跳着笑着去拥抱每一个公园里行走的人,即使它们都叫着“疯子!”匆匆忙忙的逃开他那瘦弱的臂膀。他也并不为此寂寞,在他的心中自己便是自己的寂寞芳心小姐,让仪式上的羊羔通通回家去吧!他在心中高喊着。
他试图一边嚼着那枯黄的草叶,一边向人们描述他的这种喜悦,但是所有人都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甚至同样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嘴角的枯草叶。这样的眼神确实让疯子有些害怕,但是不要紧,那是人们对枯草的偏见,他们并没有尝过不是吗?就像他们不知道一个愚人塔里的疯子是什么样的。想到这里他一下子表情凝重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是不一会儿他又蹦跳起来,几乎像玩一种新派的华尔兹。是的,他离开了愚人塔,一切都是那么的愉快,人们管那叫自由,人们为获得自由的人的欢乐而欢乐,如今却都怔怔的盯着一个疯子,对,这里我们要强调,他是一个年轻的疯子。
当疯子看到公园长椅上的忧郁男人时便有了一种强烈的亲切感,那感觉与先前的激动不同,而是十分柔软的来自男人半开的衬衣上还算新鲜的抓痕。抓痕纤细而有力道,还刮开了一些肉丝,它们即使正在上痂也并不能骗过年轻的疯子,那来自另外一个疯子。疯子这个词在这些年与他有了深深的感情,它直接命名着疯子,它是疯子的伙伴。他靠近忧郁的男人从背后抱住他的脖子,然后分享了他的一串怪异的笑声当做喜悦和友好的表示。男人并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而是惊讶的欢叫:“安娜贝尔?”这也使疯子惊讶,他用早已被遗忘的人类语言生硬的挤出一个字:“谁?”
男人回过头发现是疯子也并没有失望,而是友好的欢迎他坐下,一改忧郁的笑着说:“哦,安娜贝尔是我的妻子,她也常那样微笑。”疯子喜欢微笑这个词,那男人懂得疯子的微笑。也许是处于对自己口腔爆发出的母语的怀念,疯子又问了一遍:“谁?”男人依旧爽朗的答:“安娜贝尔啊。她是我的妻子。她喜欢把我们的沙发枕头解剖用羽毛球搭出美丽的拼图装饰我们的家。”疯子见这交谈很愉快,又问:“谁?”男人又无比开心的回答:“安娜贝尔啊,她是我的妻子,她总是无比温柔的在周三下午给我的锁骨处装上新鲜的花纹。她的手指纤细并不像其他疯子那样的强壮野蛮,我猜想你也不是。”说着说着男人笑了起来,对自己的疯妻子略带自豪而又温柔,疯子接着问:“谁?”男人愉快的回答:“安娜贝尔啊,她是我的妻子,她曾在友人聚会上打翻了一整瓶果酱并在墙上用它们画画,你知道吗?那些友人都讨厌她干这样的事,但那确实是很好看的画,我有个不错的妻子。”男人和疯子就这样对话,他们相视笑着,开心的谈论着谁?一个叫安娜贝尔的疯子,男人的妻子,关于她有名字令这里很多疯子嫉妒。
夜幕慢慢越来越深了,没有围栏的小公园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男人开始主动说话:“嗨,年轻人,你知道日月共面吗?”疯子摇摇头,男人继续说:“安娜贝尔对我描述过,她说她害怕,太阳和月亮几乎同时的挂在这个小公园的天上了,天空开始扭曲,月亮被同时出来的太阳照成了腥红色。你知道吗,那时她多害怕吗?我为自己帮不了她而难过,也许这种恐惧该赐予我,她是如此善良优秀的人。接着她说,她受不了了便趴在了那片枯草上,她说那草的味道很甜,但是他们都说她疯了,要送她去愚人塔去。”疯子吐掉了快咀碎的枯草并未注意到愚人塔这三个字,他习惯性的问:“谁?”笑着等着男人说那些美好的他向往的生活。
可是男人哭了,他的声音在泪水中颤抖:“安娜贝尔啊,她是我的妻子,他们要送她去愚人塔。你去过愚人塔吗?那不是一个人待的地方啊……”疯子愣在那里,也许他在想是谁送他去哪里的,他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找不到任何一个从前的一段记忆告诉他,他是如何变疯的。于是他开始抓着自己的头发比男人更猛烈的哭,男人望着他停止了哭泣,他哭了好久,久到公园里的围栏被人遗忘,久到被嚼的面目全非的枯草静躺在一边。他问“谁?”男人答:“安娜贝尔。”可那绝望而欢欣重获自由的年轻疯子只想自己的名字。“谁?”他又问了一遍,另一边那个关爱疯子的正常人又开始哭泣。
疯子这个不被世界所接受的群体像公园里的丑恶围栏一样让人们遗忘了,即使他们努力争取从愚人塔中逃脱获得了自由也一样弥补不了那种伤痕,人们并不想理解疯子的世界,甚至让关爱疯子的人绝望,人们让不断的新疯子走进与世隔绝的愚人塔,也忘记了摇过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