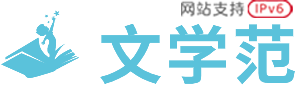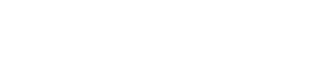我觉得现实中有着我无法打破的诅咒,在我生命中以最适的比例——
呼出又强迫吸入这具属于我的身体。
现在的我在世纪之钟敲响之前,一派颓靡。
任凭强风灌耳,寒气袭身。
黑浅,我忽然想起了你。
right here,right now。
记忆中,我亲手将你送进了历史的火坑,然后便是一瞬的高涨的火焰,弥漫血液中铁离子的味道,在安静的燃烧中,你竟全然不反抗,不挣扎,不哭泣,不怨恨,就这样在火息嗞然下,忽地化作了漫天的亮点。
迎风飘摇了我十六年的回忆。
黑浅,你是十六年前包括十六岁的我。
可我还是硬生地磨去了时光的痕迹,亲手葬了你。
黑浅,你是你辉煌纯深的过去,是我现已无法用失败者的身份染指的荣誉。
但不知,是否在这繁华锦世的假象中我应向你致以深深的歉意。
当然,前提是,你不是我迷失的原因。
你总是野心勃勃的迷恋着第一的位置,然后不顾一切奔赴战场,不惜牺牲这沉冷世间的暖阳,去安抚你内心不为人知的创伤。
最后,你成了角逐的王者,毅然改变了人生的斜率,平行渐远了交点的暖阳。
这刻薄世上你最暖的笑,这凉情人间你最美的眸,我都深爱着,我生命中而又消失了的少年。
黑浅,你看,你还是写给了你自以为是的纯深的爱情。
黑浅,现在我已无法寻到回忆空白中的你。
难道,因我当初果断的抛弃,在火焰中沉默的你,终于不甘心的逃窜了一缕,装点我踌躇满志的十七世纪满是荒凉的气息。
幻作这世纪之旅中盛大的假象奇迹。
后来是,你是我迷失的原因。
我竟轻易成为失去思想的芦苇,载着一位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
但,
这注定了我即将结束的十七的失败,但也预示这未来我十八世纪的成功。
诅咒曰:假象与真,失败与成,循而复往,不破不灭。
岁月明灭中,是谁写下了诅咒,是谁为了名利埋掉了过去,是谁又幻作假象迷失了国王,是谁念念不忘着历史,导演了今天的悲剧?
又是谁在此执笔,否认现实的残酷,只写下逃避?
黑浅,原来你从未消失,从来都是我身上不能抹除的烙印,在残酷冷血的世界中时刻麻痹这我的神经,无声的编织着巨大的假象,笑看着我在仓皇中呻吟挣扎。
一派颓靡。
你仍不会选择死亡,因为他们是你心底最在乎的东西,你深爱着他们。
可是,黑浅,他们是谁?
诅咒曰: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名利,功名利禄,阿谀奉承。
黑浅,他们竟是你深爱的东西,抑或是十六年前以至于这十七世纪我一直至爱的东西?
那么,在这执笔的,亦是这十七世纪尾巴上的我?
only myself。
强风终于洞察了我的耳膜,以强横的姿态肆虐这我生命中仅有的气息。
我似是看见寒气缭绕,黑荆遍野的血红。
颤抖着,
呼唤光明。
路漫漫,阴暗处开出纯色的白花散着讽刺与嘲笑的气息,顽固的爬到我的背上一点点不留余地刺进骨髓,沉淀为阴暗灰蒙的因子,抑制着神经的传递。
柳暗花明,彼岸前铺满黑色荆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假象,不饶地缚着我的手臂一点点不带感情刮破心脏,融合为黑色繁华的假象,应示着诅咒的言曰。
最后,我成为这十七世纪末的失败与失心的loser。
the only loser。
我只能仓皇的逃向早已预见的十八世纪。
我不想以“逃”这样狼狈的字眼去更显我狼狈的身影。
可我,
毫无办法。
“咣”
“咣”
“咣”
开始了。
这来自时光辗转,世纪交替的声音,无需这破败流血的耳朵。
这是灵魂深处苏醒的叠音。
比如我,比如黑浅,比如诅咒,
我们是安静的,而又同样的沸腾。
十八世纪暂被打破的假象,暂被预见的成功。
这是不是黑荆遍野时血红所祈求的光明?
然而一瞬间,
我竟觉得这就像,现在漫天的黑夜是将我囚禁在恐惧,亦或给我安全的外衣?
我无从得知。
我只知道这不灭的诅咒仍以最适的比例,伴着我渐渐回复的呼吸。
明天我没有了看见太阳的权利,然后会死好久好久,我却看到了风中依旧飘摇的亮点。
黑浅说:“我就是你呀,不论过去,现在,还是遥远的未来。”
我疲惫地抬起了眼皮,可以就抵不住来自灵魂深深的就倦意,而又不甘地阖上。
刚才,应该是梦,对吧。
——还是黑夜的天下。
我仅存的嗅觉与触觉强烈证明着,证明这专属于黑夜阴冷的气息还有冰凉的空气。
“十八世纪来了么?”
空空的回音。
“哼”
这是最后一个单音节被无情的留在这苍穹中有炫目的烟火,却点燃了烟花易冷的悲凉之中。
呼吸停止。
国王死了。
可是,黑浅你为什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