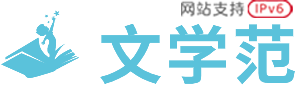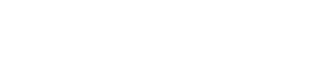云儿就是哟我的魂
魂儿随着哟风儿飘
何时飘回哟我家门
这是我母亲的歌
这是伴随我一生的歌,我还呀呀学语时,就听到了。镌刻进我的心灵,至今还在心中回荡。
这是塑造我灵魂的歌。“遥远的云,我思恋您!”这句话,这首诗,经常于我脑海中萦旋着,耳畔呼唤着。至今我在博客《高山流水翘知音》中还下意识地写下了它,我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童年。每当夜深人静,万物肃穆时,妈总是把我焐进温暖被窝,就开始了那永无了结的针线劳作。油灯如豆,在那惨淡的灯光世界中,我只看到妈那清秀的脸,脸上那对凝神的大眼,眼中那颗晶莹的泪。她哼着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这凄婉的歌声飘得很远很远,在苍茫中荡得很久很久。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似的,在这空旷的寥廓中,好像就只有我们母子两个潺弱的幽灵,相伴在挣扎,在寻觅,在呼唤.
每到夜半,我总是从甜蜜的梦中醒来。我聆听着这熟悉的“提搭”声,它不是闹钟,是我母亲织布的声音。我母亲总是哼着这歌,伴着织机的穿梭声,织着永无了结的布,直到天明。我于心不忍,当我刚够到织机时,就爬上去织布,也哼起母亲的歌,母亲笑骂道:悖时的大娃,真没出息。
有时,我扭着母亲问:我们这些云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
妈总是凝目远翘:是从天的那边,很远很远。那里有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层层水田,行行桑桐,还有——还有——我那快瞎了眼的老娘,总想看你一眼的外婆。
有时,母亲也摆起她的过去,她的小时候。
她领着一群小姐妹兄弟在月光下拍手学唱: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推糯米,娃儿闻到糯米香,打起锣儿上学堂。
有时她又带着这群娃儿在堂屋前的草坪上抓小鸡(儿童游戏),过“增增桥”。。。
白天,兄弟们跟着爷爷酿酒造纸.那酒是凤凰泉酿出来的,开槽时好香好香,飘得好远好远.那山泉就在老屋后,用根竹筒就涧过来.
女娃就纺纱织布,绷布绣花.谁偷懒了,外婆就戳着脑壳说:死娃子,不想嫁人了,想躲在家里吃一辈子闲饭,没出息。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如野鹿,快活极了。
我经常做着相同的梦,一座高高的山,一湾汪汪的塘,塘里是呀呀乱叫的小鸭子,秧田里的鱼儿蹦上我的脸。。。这是什么地方,我从未去过,为什么梦中总反复重复这些场景。上苍在冥冥中向我彰示着什么!
我出身于都市,又在闹市中长大;但我和闹市总是格格不入。我胆怯,我腼腆,我不善于和人交往,我厌恶城市的喧嚣。我想往青山绿水,想往深山老林的肃穆静谧,想往苍鹰盘旋的蓝天。
我是这个城市的另类,我在人头攒动的人海中踽踽独行。我经常独自一人爬到那东山顶去遥望那远方的云;我经常独自一人流连于嘉陵江畔,聆听纤夫那高亢的号子,还有那西山开石匠人从肺腑深处崩裂的哼哈声.
上天给了我一个好名字“乐林”。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的基因,这就是我想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