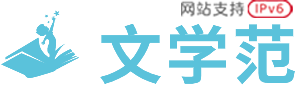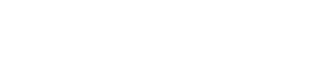吉安!
现在的时代,互联网把人拉得近了,心却远了,电话把办事的节奏提高了,人却更加的懒了。
记得上一次写信的时间好像还是大一的时候把,时间一晃,有5、6年的时间没有动笔写过信了,那时候家里穷,农村的条件差,通讯、网络都是一个神奇的新鲜事,就连那黑白电视也是房顶上架个天线,把手动频道翻来覆去的转了几十圈都是那一个点歌的地方台,时值下雨天阴什么的,还是一屏幕的满天星。现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广场上看来来往往、花花绿绿的美女也比看那时候的电视要强上100倍,然而,那时候的我们却是显得那样的傻根,电视里播个广告什么的,还忙把饭端过去望上半天,结果是把稀饭汤汤洒了一地。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娶上我们村最漂亮的吴家二丫头,然后买上一个大大的电视,再请上赖家的木匠做上一张大木床,没日没夜的躺在床上看电视,夏天的时候不用再摇那破竹扇子,旁边放上一个落地的电风扇,一个劲的吹。不过那时候感觉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热,扯上几尺花布,妈妈一针一线的缝上一条裤衩子,然后一套,光着上身就满世界的跑了,裤衩子脏了的时候,就连人带裤子跳进河沟,从水底抓上几把淤泥裹在裤子里几搓,再在水里面一涮就干净了,然后脱下来光着*爬山岸,找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晒上,等在河里面泡上一阵子,小裤衩也干得差不多了,再爬上岸穿上裤衩,到水枯的石头下面去抓螃蟹。而现在,成天坐在凉爽的办公室还是不自在,可能是人比小时候害臊了,每天西裤皮鞋的,形同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整天的把自己装在套子里。
刚出家到外面来念书的时候,天南地北的与家人相隔几千里,只要一听说附近的村子谁谁谁到北方打工回来了,您总是急匆匆的赶过去,问别人北方的气候怎么样呀?那里的人们吃得饱吗?街上会不会很乱?最后反倒是打工得来了兴致,搬上一根长凳子,二人就坐在上面开始谈起了北方,什么那的少数民族人很多啊,治安很乱啊,人们出门腰里都是别着刀子啊,害的母亲是哭了几天几夜,越是得不到我的消息越是急,您也是一天好几次地往乡上的邮局跑,看看有没有我的来信,后来就连邮递员都烦了,只要看见你一去就说:“信都在墙上布袋里,你自己去找,有就拿。”春节回家的时候,在我的一再正确详细地描述下,母亲一听那边还不错,心底才宽慰了不少。而那时候我基本上就成了全家的心理寄托,您本不是很硬朗的腰却在外面挺的直直的,见人就开始给别人吹起了新疆是怎样的怎样,好像你是刚从那边渡完假回来了一样,而当我再一次回到家时,我的身边也不自觉开始多了一圈来向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人,这一听不打紧,我发现您把我给你讲的北方又添油加醋的给别人吹了一番,这时的我却再没有心一遍遍的去解释了,只顾着频频点头,不停的称新疆好。在每次临行前,您总是再三叮嘱我:到学校了记得多给家里写信,我总是满口答应。而到学校,发现写信已经很落伍了,别人都开始煲起了电话粥,而我在您的一封封来信问候下,却是以学业忙应付了过去,此时您却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您太相信您的儿子了,您认为儿子嘴里出来的话就是真理,而此时的我,在您们的深切期望下,却开始慢慢的一步步走向了学业上的堕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开始泡网,开始打游戏,甚至开始泡女孩了,手也一次次的向父亲你伸得更勤了,我总是变换着借口要买这门书要学那门艺了,而你却反而更加高兴了。
几年的艰难苦熬下,终于从学校毕业了,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装上了电话,安装了有线,家里也换上了彩电,(要是按我儿时的梦想算,现在的资本够娶上两个吴家的二丫头),你们也开始慢慢的了解外面了,村里当年的裤衩伙伴也一个个的走向了大城市,而此时的你,反而却是愁了起来,又是一遍遍的打来了电话,催促着我考公务员,催促着我谈对象,而此时,我却开始觉得你是不理解儿子了,而此时我却厌倦了你们开始仰慕的城市生活了,我却想与世无争了,我却看不惯阿意奉承了。我也懒得再打那电话了,电话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办事或是联络的工具了,我反而是怀念起了那久违的书信,那付诸笔尖的亲情、感情,只有在纸上才能孜孜不倦的流淌,那心底久违的冲动的泪水只有在无声中才能痛快地宣泄。虽然这是通过电脑打出来的,但是此时,我却找到了那种从未有过的绵延、感怀。
说到此时,我更想向您说的是: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谢谢你从小对我的严厉,谢谢你从小让我们写作、炼字,才有了今天的能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反而感觉到你才是我心中的骄傲,而我只是你伟大举措下的一个结晶。我也明白你的期望:希望我能在你们所认为好的人生道路上一片辉煌、光芒万丈。但是我却还想说:爸爸,你的儿子已经不小了,他也找到了他人生的坐标点,他正在往着他的幸福、往着他的美好未来前行,或许,他的未来不在城市,或许,他的未来不是舒适、明亮的办公室,但是,那却是他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