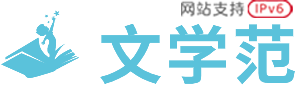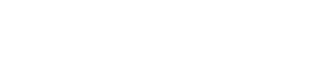在他十七岁的那个夜晚,电闪雷鸣,一个年轻的旅人敲响了古堡的门。旅人在躲雨时看到了他的脸,惊呼他有着一张不属于人间的面孔,并主动为他做了一幅画,作为让他避雨的谢礼。
又是十年过去,老管家死了,没有读过的书也所剩无几,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到外面去看看。带着他旧时代的笨拙的礼仪与服饰,还有那张依然年轻的面孔。
时间过的很快,一百年过去了,两百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划开的伤口会迅速长好,从来没有疾病困扰着他,哪怕正面被大炮的炮弹所轰中,一夜之间,滑出腹腔的肠子会重新回去,弹出眼眶的眼球也会重新长好。简而言之,他是不死的。
他不知这永生是上苍的恩赐还是魔鬼的无尽惩罚,只能略带疲倦的想着:“我们死命的攀附着几片木头,为的是尚能再多看一眼这个世界从这头到那头的流血演出,而不至于身陷其中。”
他经历了很多女人,他总是毫无感情的对着他们念着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念到:
“要不然,世俗的诽谤离间不了我们,
Men could not part us with their worldly jars,
任风波飞扬,也不能动摇那坚贞;
Nor the seas change us, nor the tempests bend;
我们的手要伸过山岭,互相接触;
Our hands would touch for all the mountain-bars
有那么一天,天空滚到我俩中间,
And, heaven being rolled between us at the end,
我俩向星辰起誓,还要更加握紧。 ”
女人们却总是在意他充满魔力的年轻容颜。
有一天,经过一家画廊,他惊讶的认出里面很多画像居然是他曾经那个城堡里的,询问之后才知道,古堡早已损毁,被探宝的人们搜刮一空,几经辗转,这些画又回到了他的手上。
夜里,他点上蜡烛,给自己倒了一杯波尔多。看着那些画,回想着苍白如纸的开始。
突然,他看到了那副旅行者给他画的画像,发现上面是个苍老如同骷髅的面孔,一瞬间他明白了。上帝的一个小失误造就了这个故事,他永远年轻,而画像中的自己代替自己老去……
第二天,收拾房间的大婶发现了一滩在地上的灰烬,还有一副自画像。画像上的人有着苍白而年轻的脸和忧郁的神情,栩栩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