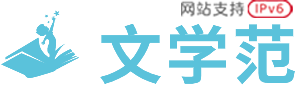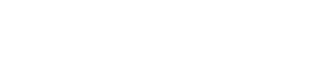但是,终究还是会来的。不一会儿,那般难忍的口渴又侵袭而来。我拍着已见空底的“王老吉”罐子,长长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妈妈说吃完晚饭带我去看医生,叫我怎忍得住?但是,我得忍呀!毕竟得先犒劳犒劳这肚子,早已咕咕叫了。
停车,下门。
我走进平安诊所,挺空。坐在医生前,我记得上次就医已经是longlongago了。我傻傻地坐在那儿。妈妈拍了拍我的肩,如梦方醒!
“来!啊――!”我张大嘴巴,两根棉签压在舌上,痒痒的。“来!做深呼吸!”我还未点头,医生便已将听诊器放在我胸前。静静地,我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去做皮试吧!”不会吧?怎么这么倒霉啊!还要挂吊针?我晕!
那根针闪着弱弱的寒光,心理防线第一道被攻破,第二道正在顽强抵抗中――毕竟好久没看见过针了,久别重逢的兄弟啊!来吧!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说时迟,那时快,那针是白的进去,红的出来。那鲜红的血液啊!
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雨如此短暂?这也真是的,害我等到花儿又开了。
现在,定时炸弹安装成功,我方已夺回阵地。在那黄土高坡上,扬起我的一张风帆,渐行渐远。
我坐在床上,左手正挂着吊瓶,右手不停地写着作业。悬梁刺骨是怎样练成的?告诉你吧,就像我这样,上悬个大号针头,下锥着一个笔尖头。原来生病是这么痛苦。下一次,我一定乖乖吃药,还我一个好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