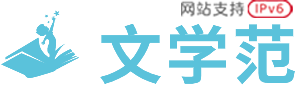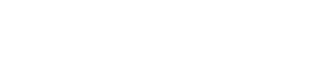记忆里的色彩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白色,医院里的纯净白色,令人绝望的白色。
我生下来耳廓就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残缺,对于一个女孩子却是致命的。我害怕鄙的目光、同情的眼神,只能剪齐耳的短发,把残缺深深地深深地藏匿起来。
一次秋季的午后,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同龄的孩子嬉戏。她们扎着马尾.无忧无虑地笑着,头发随着欢快的蹦跳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她们是那样健全而活泼,残缺而孤僻的我在她们之间,就像阳光照晒不到的地方里的一轮残月,那么异样。
一抹火红跃人我的眼帘,是新移栽的枫树。它们瘦而光滑的树干,像水墨画中苍劲有力的几笔白描,在宣纸上洒几滴血泪,便是火红的枫叶。那样纯粹的火红惊艳了我的双眼,几乎在我黯淡的眼角燃烧起来。
我飞快地跑下楼,踞起脚采了一片枫叶,放在掌心细细描画它清晰的纹理,炙热的触感温暖得让我几乎落泪。
我多么希望我的生命能像它一样火红。
妈妈又带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我的耳骨还没长定型,不能做手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粉刷得雪白的墙壁,整洁而干净的白色床单,我的脸色一定也是这样的惨白。周围整片的白色让我喘不过气,我垂下眼睑,看着手心皱皱的枫叶,它还是那样火红,仿佛一枚掉落的火种,迅速地将这片白色燃烧殆尽。
晚上,雷声吓得我睡不着,我跑到阳台,看到浑浊的天地间,一抹火红傲然独立。雨点打在枫叶上,它兀自将不屈的火红蔓延,似乎要将天空撕裂,将我的忧伤也一并撕裂。
我握紧了手心的枫叶,手轻轻抚摸着残缺的耳廓,不住地颤抖,心里却已有些许释然。
第二天,我让妈妈把我耳边的头发夹上去,然后牵着她的手走出门。同楼的大人们看到我耳朵时眼中都闪过惊讶,我只是灿烂而自然地笑着,他们便也微笑着摸摸我的头。
没有人会嘲笑我,只要我的生命火红得足够让他们忘记我的残缺。
起了一阵秋风,枫叶簌簌落下,雨过灰白的天空被映衬为迷人的火红。
我改变了生命的色彩,在生命中点染出一片又一片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