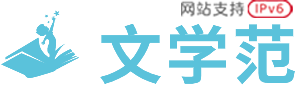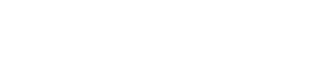夏日未至,拂面的风中仍蕴有些许春日的妩媚,顽皮的阳光竟先发制人,毫无遮拦地射向人们敞露的脸庞,焦灼得骇人。矮矮的站牌下伫满了等待的身影,被晒得滚烫的心不约而同地急躁着,翘首期盼公交车姗姗来迟的倩影。我斜倚在站牌上,正欲闭目小憩,身边的人群突然向前涌动起来——啊,28路来了!我耸了耸疲惫的肩,还未迈步,便被拥挤的人流推上了车。正值上班高峰期,车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无奈中只能紧紧地攥住扶手,以寻得一方立足之地。伴着车的一停一顿,羸弱的身躯开始支持不住混沌的头颅,大脑像被搅浑了的浆糊,昏昏沉沉地耷拉下来,肩上的书包亦止不住地下坠,愈发显得沉重。“呐,你坐这边来吧。”影绰中有沉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只见一只厚实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肩。如一只绝境逢生的羊羔,我从喉头挤出一句干涩的谢谢,便不假思索地坐了下去,靠在椅背上,吁着气,惬意地欣赏起沿途的风景来。
“倏”得一声,臃肿的公交车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警戒的红灯前。窗外刺鼻的汽油味令我作呕,皱着眉将头扭向车内,啊——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怎样触目的一幅场景啊。就这么一只形同虚设的袖子,无力地下垂着,空空荡荡,荡荡空空,轻微的晃动中捕捉不到丝毫生气。它没有需要被遮蔽的肢体,没有任何坚硬的支柱,仅仅是——仅仅是为了掩盖那因不幸而秃败了的断臂!袖口褶皱着,我心上的叹息偱着袖子而上,目光所触及的,却是那样分明的棱角,虽纵横了沟壑仍不减坚毅的方形下颌。五官平平淡淡,并无丝缕傲人之处。但透过窗扉铺设在他脸上的阳光却莫名地缱绻着,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这光彩的另一端,是一只属于劳动者的厚实的手掌——那轻拍了我的肩的手掌!它缄默地紧攥着冰冷的扶手,嶙峋的关节因过度用力而突兀地发白。我的心抽搐着,给我让座的,竟是他——是这样一位为生计而苍老了的残疾人!车上的人声嘈杂依旧,此起彼伏着的是操着四方口音的谈天声,通话声,而我却不合时宜地哑然了。窄窄的内心似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涩,惘然不知所味。我用沉默的目光注视着这坚忍的脸庞,揣测究竟是怎样炽热的心造就了这般奇异的光芒。我无从知晓是怎样的勇气使他剥落了内心的苦楚,亦无从知晓这样的一抹微笑中掺杂着多少生命的沉重。他似乎觉察到了这异样的注视,侧头对我微微一笑,脸上的皱纹欢快地游动着,里面嵌满了阳光,如同春日里明媚的阡陌。
我愧然地颔首凝视起自己晦昧的内心来。不假思索的落座,似乎理所当然地被关照,以一句肤浅的谢谢来回馈一份真挚而纯粹的奉献。某种无以言说的情绪软软地哽咽在喉头,似被污物堵塞了的下水道,找不到合理的出口。身体的残疾并不足以成为沟通的屏障,他上扬的嘴角中折射的自信与善良暗喻着那下垂的空袖中盛满了希望!我笑了,理了理额角的散发,上前轻声说:“叔叔,您坐吧。我不晕车的呢。”他的面颊因惊愕而略显僵硬,“啊,不——不用了。我的身体硬朗得很呢!我刚才看你有点晕车啊……所以……”枯槁的脸竟在言语间泛起了几许红晕。他的手掌仍紧紧地攥着摇摆的扶手,也紧紧地揪住了我的心。四目对视间,抿嘴一笑,一汩暖流涌上心头,温润了我狭兀的心房,绽起一朵朵清丽的小花。
“露亭宾馆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清脆的女音缓缓响起,随着人流下车。拂面的风儿依旧妩媚,只是落在身上的阳光削减了它焦灼的意味,就这么软软地,软软地,荡漾在心坎。不温不火的气息仿若那偶遇的残疾人叔叔,把伤痕当酒窝,在生命的晦暗处不忘扬起最美的笑容。以人性的本真填补身体的残缺,执阴霾之笔,绘明媚之景。恍然之间,照彻了自己,更温暖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