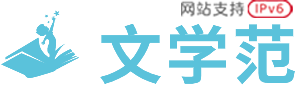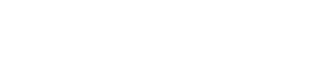“葫芦”就是张红路。她的笑声与众不同,总是“咯咯,嘿嘿,哈哈”的,颇有韵律,常常引得别人也跟着笑起来。初二时,我和她同桌。我俩前边坐着班上大名鼎鼎的滑稽鬼谢斌,尽出洋相,逗得“葫芦”笑个不停。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小疯丫头,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我喜欢“葫芦”不仅仅因为她笑得甜美,还因为她是文艺之神缪斯的宠儿。她弹得一手好琵琶,我听过她弹《春江花月夜》,那醉人的琴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萦绕。她也爱唱歌,嗓音圆润、柔和,《清晨》一曲,唱得尤为出色。她还爱跳舞,新中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活动中,她是我们班集体舞的小教练。
但是,有一天,这个似乎从来不知忧愁滋味的姑娘,脸上却笼罩了一层愁云。那天要考语文。早晨,同学们坐在座位上,人人面对一本语文书,不停地念呀背呀。可“葫芦”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做几何题。我不由得轻声问道:“复习完语文啦?”“葫芦”抬起头,脸上泛起一层阴云,没有回答。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从她脸上找到笑容,于是我又问:“你怎么啦”“我妈挡住屋门,不让我拿语文书。”她说,语调是那么压抑。我不知所措,慌忙把自己的语文课本推了过去。她向我点了点头,嘴角掠过一丝感激的微笑,但一闪便消失了。
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回,戴彬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地,谁劝也不行。“葫芦”凑过去,在她耳边低声细语。不大一会儿,戴彬抬起头,擦干了泪水。“这就对了,别耍小孩儿脾气了,我的‘娇小姐’,笑一笑。”“葫芦”在引逗她,戴彬果然破涕一笑。
现在,这个自己从来达观乐天,而且又善于为别人分忧解愁的姑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遭受了什么难言的痛苦?我被关进了“闷葫芦”。
一个偶然的机会,帮我打开了“闷葫芦”。作文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自传》。经“葫芦”允许,我拿过她的作文本。原来,她上小学三年级时,妈妈得了精神病,后来爸爸又被判五年徒刑。家里,就靠她照顾患病的妈妈。精神病人喜怒无常,“葫芦”为了让妈妈高兴,常陪她到公园散步,但一路上却往往无端地挨骂。唉,“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真替“葫芦”感到委屈。可是,我更从心底里佩服她,她在自传中写道:“只要地球还转,我就要笑着生活下去。”
的确,她是笑着生活的。她从音乐旋律中获得了安慰,从文学形象中汲取了力量。有一次,我俩在幽静的小花园中散步,谈到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我喜欢简?爱,她不漂亮,但有个性,勇于和命运搏斗……”“葫芦”一边沉思一边轻轻地说,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着坚毅的光芒,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动。
红路坚强的性格像简?爱,但她的命运毕竟与孤儿院中长大的简?爱不同。她遇到了另一位“好妈妈”——班主任武老师。武老师帮她管理生活费,什么时候添置鞋袜,星期天怎样度过,都替她想到了。她还有另一个“家庭”——学校,学校破例允许这个初中生住宿,每逢佳节,同学们便凑钱买些生活必需品送给她,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被,东西虽少,情义却重。
红路满十五周岁了,同学们聚在宿舍里向她祝贺生日。夏雪把一个粉红色纱裙的洋娃娃举到她面前:“看,她笑得多甜,和你一样,让她陪着你吧。”刘颖送给她一本蝴蝶信笺和一些邮票,搂着她的肩膀低声说:“收下吧。给爸爸妈妈写信用得着。”小小的房间里充满青春的活力,“葫芦”笑得更美更甜了。春风把笑声吹出窗口,洒向校园,洒向远方。